天门,长江中游的“王者之城”?
天门,长江中游的“王者之城”?
天门,长江中游的“王者之城”?禹划九州,始有荆州(jīngzhōu)。《尚书·禹贡》记载:“荆及衡阳(héngyáng)惟荆州。”古荆州囊括从荆山到衡山之南的广袤土地(tǔdì)。但很多史学家认为九州只是一段神话。
1954年,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镇附近正在修建水渠,工人们在泥土之下,发现了大量陶片。经过考古学家鉴定(jiàndìng),这些陶器来自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时代,而传说中禹划九州的时间正是在这一时代。同时,天门地处荆山南部(nánbù),正与(yǔ)古籍中记载的古荆州(jīngzhōu)地貌范围吻合。
难道真实的(de)古荆州就隐藏在这片土地之下?此后(hòu),考古学家在石家河镇陆续(lùxù)发现众多史前遗址点,这些遗址点宛如(wǎnrú)一颗颗遗落的明珠,串联起来后,竟勾勒出一个范围超800万平方米的巨大史前聚落,成为当时全国范围内发现的最大的史前遗址群之一。
居住(jūzhù)在石家河的先民们曾经过(guò)着怎样的生活?经过七十余年的持续考古发掘,石家河文化遗址如何深深融入天门这片土地?

石家河(shíjiāhé)遗址早期出土的陶偶
寻找长江中游“第一(dìyī)古城”
对石家河遗址群文化面貌的初步认识引起了著名考古(kǎogǔ)学家、时任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严文明的关注(guānzhù)。
在他的(de)推动下,1987年6月,北京大学考古系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(hé)荆州博物馆联合成立石家河考古队,对石家河遗址群进行有计划(jìhuà)的考古调查和发掘。
1990年春天(chūntiān),考古人员走到位于石家河(shíjiāhé)遗址腹地的(de)一座河堤,窑厂的工人们把堤挖开了一个缺口,考古人员从剖面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人工夯筑的不大规则(guīzé)的层理(cénglǐ)。通过对夯层中采集的陶片进行年代测定,并结合对堤坝修筑工艺的研究,考古人员最终确认,这座河堤其实是石家河先民筑造的城墙。
沿着这道城墙,勘探向四方延伸。结合对整个遗址群地形地貌的(de)仔细考察,以及对各处遗迹遗物的缜密(zhěnmì)分析,一座史前巨城轮廓,终于在世人(shìrén)面前清晰起来:城址是不大(bùdà)规则的长方形,总面积达120万平方米(wànpíngfāngmǐ)。高大的城墙外面环绕着宽大的壕沟,壕沟围成的面积达180万平方米。这样的规模,在龙山时代是首屈一指的。
城垣确定后(hòu),一幅石家河遗址群的图景(tújǐng)清晰地(dì)展现在人们(rénmen)面前。此前发现的那些遗址点,都有了具体身份:神圣的祭祀中心、热闹的居民区、静默的墓地……一幅高度发达的长江中游新石器晚期文明图景,在江汉平原上生动铺展。

但这次发掘依然有一个遗憾:考古人员仅找到了古城的西城墙和部分(bùfèn)南城墙。东城墙与(yǔ)北城墙,如同消失的拼图,隐匿在历史迷雾与地理变迁之中(zhīzhōng)。
遗憾在三十年后得以弥补。当年参与石家河城址发掘的(de)年轻考古(kǎogǔ)(kǎogǔ)人员中,有一位(yīwèi)名叫方勤的北京大学考古系(kǎogǔxì)学生。2022年,当新一轮“中华文明探源”和“考古中国”项目启动,已成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的方勤,肩负起总领队的重任,带领着北京大学与天门博物馆的团队,再次对石家河遗址展开全面系统调查和勘探。

这(zhè)一年秋天,考古(kǎogǔ)(kǎogǔ)人员在打下的探铲中发现了黄色泥土。这正是史前筑城的关键原料,此前发现的城墙皆由黄土堆筑。东城墙找到了!不久后(hòu),考古人员又在石家河遗址的北侧发现了最后一段城墙,一个完整的石家河古城“重现”。
2023年3月,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首次确认,石家河(shíjiāhé)古城由内城、城壕(护城河)、外郭城(guōchéng)构成(gòuchéng),总面积达(dá)348.5万平方米,为长江中游同时期最大的古城,与长江下游的良渚古城规模相当,是长江中游面积最大、等级最高、延续时间最长的史前古城。
推翻三星堆人像(rénxiàng)外星说
石家河古城的形成,标志着长江中游以石家河为核心的统一的文化共同体正式形成,它与长江下游的良渚王国一起,几乎同时向外扩张(kuòzhāng),并北上中原,影响全国,是长江流域本土文化最为辉煌(huīhuáng)的时期(shíqī)之一。
石家河遗址开创“早期中国”制造(zhìzào)技艺多个“第一”,玉器制作是其最突出的代表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(kǎogǔ)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(xiāng)曾评价道(dào),石家河文化玉器,标志着一个史前玉作的巅峰,代表了一个中国玉文化发展空前绝后的时空坐标。
有“中华第一凤”之称(zhīchēng)的玉团凤,被认为是凤文化重要源头。1955年,考古人员(rényuán)在对石家河罗家柏岭遗址进行(jìnxíng)发掘时发现了(le)这件玉团凤。因它的制作技术高超,当时考古界不敢相信它与粗糙的土陶共存于同期的史前时代,初步判断它属西周遗物。直到上世纪80年代,石家河肖家屋脊又发现一批(yīpī)玉器(yùqì),这件玉团凤的年代才被修正为新石器时代。
更令人称奇的是,它(tā)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凤,是凤鸟“姐妹花”。经(jīng)考证,妇好墓出土的玉凤在工艺(gōngyì)、造型均与石家河玉团凤极为相似,即使相隔时间久远,但妇好玉凤或与石家河玉团凤同源。

在石家河遗址的发掘中,曾出土玉(yù)器共计近500件,包括人头像、龙、凤、鹰、虎、蝉等造型,这些玉器不仅类型丰富、形态(xíngtài)优美、造型生动(shēngdòng),而且技术精湛,其普遍使用的圆雕、透雕、减地阳刻、浅浮雕线刻(xiànkè)等工艺,代表了史前中国乃至东亚地区(dōngyàdìqū)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水平,改写了中国玉文化历史。
石家河玉器的(de)(de)身影,出现在北方的石峁遗址、陶寺遗址,甚至山东的新石器遗址中,无声地诉说着(sùshuōzhe)石家河文化强大的辐射力,成为文化上“早期中国”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石家河遗址出土(chūtǔ)的部分玉器
2024年2月,武汉盘龙城(pánlóngchéng)遗址博物院“玉神——石家河玉文化特展”汇聚来自凌家滩、良渚、陶寺、石峁、三星堆、金沙等多个(duōgè)重要遗址的文物(wénwù)珍品。在展厅的醒目位置,石家河玉人头像与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铜人头像并列(bìngliè)陈列(chénliè)。尽管二者的材质、大小不同,但一种跨越时空的“神似”却扑面而来:均“佩戴”辫索状发箍,都具有双耳穿孔、菱形或梭形大眼、蒜头鼻或鹰钩鼻、阔嘴和(hé)短颈等特征。
考古研究表明,三星堆文化晚于石家河文化,其青铜人像形象与石家河玉人像高度接近。这(zhè)强有力的联系,让三星堆青铜人像来自外星人(wàixīngrén)的说法不攻自破。方勤曾(céng)在媒体采访中表示(biǎoshì),石家河玉器一定是文化交流(jiāoliú)的结果。那是一个进入了文化交流、文化认同的时代,永远不要(búyào)低估古人的交流、交融的能力。中华文明生生不息,从未间断的密码是什么?就是交流。
石家河文化已融入(róngrù)天门人的日常
石家河遗址(yízhǐ)的(de)(de)发现,为追寻(zhuīxún)长江中游文明打开了(le)一扇窗,实证了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一样,都是中华文明的起源,共同构建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。其价值备受认可:2020年列入“考古中国”“中华文明探源研究”重大课题,2021年入选“百年百大考古发现”,2025年入选国家首批重要大遗址清单。
探索远未止步。如今在石家河考古遗址(yízhǐ)公园内,考古工作者们仍在追寻古国中“王”的(de)踪迹,破解先民应对水环境的智慧,探寻高等级建筑的奥秘,梳理玉器陶器背后(bèihòu)的文化交流网络。
而石家河(shíjiāhé)文化遗产(wénhuàyíchǎn),早已融入天门人的(de)日常生活。天门是全国首个蒸菜之乡,“家家会做蒸菜、人人爱吃蒸菜”的城市记忆就起源于四千年前的石家河文化。凤鸟图案也频繁出现在天门手艺人的作品中,成为(chéngwéi)独特的文化符号。
如今,天门即将新增一座让石家河文化“活起来”的载体。2017年,石家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被国家文物局批准立项。2024年,位于遗址公园南部环岛内的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动工开建,预计今年10月底(yuèdǐ)完成主体工程建设。届时(jièshí),这座象征(xiàngzhēng)“城”的方形(fāngxíng)建筑,将让踏入者开启一场穿越时空之旅(zhīlǚ)。

石家河遗址博物馆规划图(guīhuàtú)
据天门市石家河遗址管理处副主任徐同斌介绍,馆内以“长江之光,文明之源”为主题,将打造玉器工艺(gōngyì)专题陈列,集中展示包括(bāokuò)神人头像、连体双人玉玦、玉虎、虎座双鹰佩等石家河玉器。更富创意的(de)(de)是“撞脸文物”对比展区,将石家河文物与与全国其他重要遗址出土文物并置,让(ràng)观众感受长江与黄河流域的文化互动。
为营造“临场感”,博物馆将利用先进技术实现石家河(shíjiāhé)聚落的(de)“可视化”。巨幅遗址分布图与精细(jīngxì)的城垣复原模型(móxíng),将让面积超300万平方米的史前都城尽收眼前。三房湾遗址出土的200余万件红陶杯残次品,将再现长江中游最大(zuìdà)史前“制陶工厂”的壮观场景(chǎngjǐng);印信台遗址出土的套接陶缸群、彩陶纺轮纹饰(wénshì),将带人重返先民祭祀的神圣与日常的烟火。借助VR技术,观众甚至可以化身“石家河城主”,沉浸式漫游鼎盛时期的长江文明之都。
从1954年铁锹下第一枚(dìyīméi)陶片的惊现,到如今博物馆(bówùguǎn)穹顶下玉器流转的微光,七十余载考古接力,终让长江中游的“王者之城”重现。而当石家河遗址博物馆的大门开启之时,长江中游的史前文明(wénmíng)故事(gùshì),将从天门出发,传向更广阔的世界。
1.严文明:《石家河考古(kǎogǔ)记(jì)》(代序),石家河考古队编《肖家屋脊》,文物出版社,1999年
2.方勤 :《深切缅怀严文明先生——忆先生与石家河(shíjiāhé)二三事》,《江汉(jiānghàn)考古》, 2024年第3期
3.戴伟:《北大考古(kǎogǔ)与“百年百大考古发现”|石家河新石器时代遗址群》,澎湃(pēngpài)私家历史频道

禹划九州,始有荆州(jīngzhōu)。《尚书·禹贡》记载:“荆及衡阳(héngyáng)惟荆州。”古荆州囊括从荆山到衡山之南的广袤土地(tǔdì)。但很多史学家认为九州只是一段神话。
1954年,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镇附近正在修建水渠,工人们在泥土之下,发现了大量陶片。经过考古学家鉴定(jiàndìng),这些陶器来自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时代,而传说中禹划九州的时间正是在这一时代。同时,天门地处荆山南部(nánbù),正与(yǔ)古籍中记载的古荆州(jīngzhōu)地貌范围吻合。
难道真实的(de)古荆州就隐藏在这片土地之下?此后(hòu),考古学家在石家河镇陆续(lùxù)发现众多史前遗址点,这些遗址点宛如(wǎnrú)一颗颗遗落的明珠,串联起来后,竟勾勒出一个范围超800万平方米的巨大史前聚落,成为当时全国范围内发现的最大的史前遗址群之一。
居住(jūzhù)在石家河的先民们曾经过(guò)着怎样的生活?经过七十余年的持续考古发掘,石家河文化遗址如何深深融入天门这片土地?

石家河(shíjiāhé)遗址早期出土的陶偶
寻找长江中游“第一(dìyī)古城”
对石家河遗址群文化面貌的初步认识引起了著名考古(kǎogǔ)学家、时任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严文明的关注(guānzhù)。
在他的(de)推动下,1987年6月,北京大学考古系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(hé)荆州博物馆联合成立石家河考古队,对石家河遗址群进行有计划(jìhuà)的考古调查和发掘。
1990年春天(chūntiān),考古人员走到位于石家河(shíjiāhé)遗址腹地的(de)一座河堤,窑厂的工人们把堤挖开了一个缺口,考古人员从剖面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人工夯筑的不大规则(guīzé)的层理(cénglǐ)。通过对夯层中采集的陶片进行年代测定,并结合对堤坝修筑工艺的研究,考古人员最终确认,这座河堤其实是石家河先民筑造的城墙。
沿着这道城墙,勘探向四方延伸。结合对整个遗址群地形地貌的(de)仔细考察,以及对各处遗迹遗物的缜密(zhěnmì)分析,一座史前巨城轮廓,终于在世人(shìrén)面前清晰起来:城址是不大(bùdà)规则的长方形,总面积达120万平方米(wànpíngfāngmǐ)。高大的城墙外面环绕着宽大的壕沟,壕沟围成的面积达180万平方米。这样的规模,在龙山时代是首屈一指的。
城垣确定后(hòu),一幅石家河遗址群的图景(tújǐng)清晰地(dì)展现在人们(rénmen)面前。此前发现的那些遗址点,都有了具体身份:神圣的祭祀中心、热闹的居民区、静默的墓地……一幅高度发达的长江中游新石器晚期文明图景,在江汉平原上生动铺展。

但这次发掘依然有一个遗憾:考古人员仅找到了古城的西城墙和部分(bùfèn)南城墙。东城墙与(yǔ)北城墙,如同消失的拼图,隐匿在历史迷雾与地理变迁之中(zhīzhōng)。
遗憾在三十年后得以弥补。当年参与石家河城址发掘的(de)年轻考古(kǎogǔ)(kǎogǔ)人员中,有一位(yīwèi)名叫方勤的北京大学考古系(kǎogǔxì)学生。2022年,当新一轮“中华文明探源”和“考古中国”项目启动,已成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的方勤,肩负起总领队的重任,带领着北京大学与天门博物馆的团队,再次对石家河遗址展开全面系统调查和勘探。

这(zhè)一年秋天,考古(kǎogǔ)(kǎogǔ)人员在打下的探铲中发现了黄色泥土。这正是史前筑城的关键原料,此前发现的城墙皆由黄土堆筑。东城墙找到了!不久后(hòu),考古人员又在石家河遗址的北侧发现了最后一段城墙,一个完整的石家河古城“重现”。
2023年3月,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首次确认,石家河(shíjiāhé)古城由内城、城壕(护城河)、外郭城(guōchéng)构成(gòuchéng),总面积达(dá)348.5万平方米,为长江中游同时期最大的古城,与长江下游的良渚古城规模相当,是长江中游面积最大、等级最高、延续时间最长的史前古城。
推翻三星堆人像(rénxiàng)外星说
石家河古城的形成,标志着长江中游以石家河为核心的统一的文化共同体正式形成,它与长江下游的良渚王国一起,几乎同时向外扩张(kuòzhāng),并北上中原,影响全国,是长江流域本土文化最为辉煌(huīhuáng)的时期(shíqī)之一。
石家河遗址开创“早期中国”制造(zhìzào)技艺多个“第一”,玉器制作是其最突出的代表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(kǎogǔ)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(xiāng)曾评价道(dào),石家河文化玉器,标志着一个史前玉作的巅峰,代表了一个中国玉文化发展空前绝后的时空坐标。
有“中华第一凤”之称(zhīchēng)的玉团凤,被认为是凤文化重要源头。1955年,考古人员(rényuán)在对石家河罗家柏岭遗址进行(jìnxíng)发掘时发现了(le)这件玉团凤。因它的制作技术高超,当时考古界不敢相信它与粗糙的土陶共存于同期的史前时代,初步判断它属西周遗物。直到上世纪80年代,石家河肖家屋脊又发现一批(yīpī)玉器(yùqì),这件玉团凤的年代才被修正为新石器时代。
更令人称奇的是,它(tā)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凤,是凤鸟“姐妹花”。经(jīng)考证,妇好墓出土的玉凤在工艺(gōngyì)、造型均与石家河玉团凤极为相似,即使相隔时间久远,但妇好玉凤或与石家河玉团凤同源。

在石家河遗址的发掘中,曾出土玉(yù)器共计近500件,包括人头像、龙、凤、鹰、虎、蝉等造型,这些玉器不仅类型丰富、形态(xíngtài)优美、造型生动(shēngdòng),而且技术精湛,其普遍使用的圆雕、透雕、减地阳刻、浅浮雕线刻(xiànkè)等工艺,代表了史前中国乃至东亚地区(dōngyàdìqū)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水平,改写了中国玉文化历史。
石家河玉器的(de)(de)身影,出现在北方的石峁遗址、陶寺遗址,甚至山东的新石器遗址中,无声地诉说着(sùshuōzhe)石家河文化强大的辐射力,成为文化上“早期中国”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石家河遗址出土(chūtǔ)的部分玉器
2024年2月,武汉盘龙城(pánlóngchéng)遗址博物院“玉神——石家河玉文化特展”汇聚来自凌家滩、良渚、陶寺、石峁、三星堆、金沙等多个(duōgè)重要遗址的文物(wénwù)珍品。在展厅的醒目位置,石家河玉人头像与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铜人头像并列(bìngliè)陈列(chénliè)。尽管二者的材质、大小不同,但一种跨越时空的“神似”却扑面而来:均“佩戴”辫索状发箍,都具有双耳穿孔、菱形或梭形大眼、蒜头鼻或鹰钩鼻、阔嘴和(hé)短颈等特征。
考古研究表明,三星堆文化晚于石家河文化,其青铜人像形象与石家河玉人像高度接近。这(zhè)强有力的联系,让三星堆青铜人像来自外星人(wàixīngrén)的说法不攻自破。方勤曾(céng)在媒体采访中表示(biǎoshì),石家河玉器一定是文化交流(jiāoliú)的结果。那是一个进入了文化交流、文化认同的时代,永远不要(búyào)低估古人的交流、交融的能力。中华文明生生不息,从未间断的密码是什么?就是交流。
石家河文化已融入(róngrù)天门人的日常
石家河遗址(yízhǐ)的(de)(de)发现,为追寻(zhuīxún)长江中游文明打开了(le)一扇窗,实证了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一样,都是中华文明的起源,共同构建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。其价值备受认可:2020年列入“考古中国”“中华文明探源研究”重大课题,2021年入选“百年百大考古发现”,2025年入选国家首批重要大遗址清单。
探索远未止步。如今在石家河考古遗址(yízhǐ)公园内,考古工作者们仍在追寻古国中“王”的(de)踪迹,破解先民应对水环境的智慧,探寻高等级建筑的奥秘,梳理玉器陶器背后(bèihòu)的文化交流网络。
而石家河(shíjiāhé)文化遗产(wénhuàyíchǎn),早已融入天门人的(de)日常生活。天门是全国首个蒸菜之乡,“家家会做蒸菜、人人爱吃蒸菜”的城市记忆就起源于四千年前的石家河文化。凤鸟图案也频繁出现在天门手艺人的作品中,成为(chéngwéi)独特的文化符号。
如今,天门即将新增一座让石家河文化“活起来”的载体。2017年,石家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被国家文物局批准立项。2024年,位于遗址公园南部环岛内的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动工开建,预计今年10月底(yuèdǐ)完成主体工程建设。届时(jièshí),这座象征(xiàngzhēng)“城”的方形(fāngxíng)建筑,将让踏入者开启一场穿越时空之旅(zhīlǚ)。

石家河遗址博物馆规划图(guīhuàtú)
据天门市石家河遗址管理处副主任徐同斌介绍,馆内以“长江之光,文明之源”为主题,将打造玉器工艺(gōngyì)专题陈列,集中展示包括(bāokuò)神人头像、连体双人玉玦、玉虎、虎座双鹰佩等石家河玉器。更富创意的(de)(de)是“撞脸文物”对比展区,将石家河文物与与全国其他重要遗址出土文物并置,让(ràng)观众感受长江与黄河流域的文化互动。
为营造“临场感”,博物馆将利用先进技术实现石家河(shíjiāhé)聚落的(de)“可视化”。巨幅遗址分布图与精细(jīngxì)的城垣复原模型(móxíng),将让面积超300万平方米的史前都城尽收眼前。三房湾遗址出土的200余万件红陶杯残次品,将再现长江中游最大(zuìdà)史前“制陶工厂”的壮观场景(chǎngjǐng);印信台遗址出土的套接陶缸群、彩陶纺轮纹饰(wénshì),将带人重返先民祭祀的神圣与日常的烟火。借助VR技术,观众甚至可以化身“石家河城主”,沉浸式漫游鼎盛时期的长江文明之都。
从1954年铁锹下第一枚(dìyīméi)陶片的惊现,到如今博物馆(bówùguǎn)穹顶下玉器流转的微光,七十余载考古接力,终让长江中游的“王者之城”重现。而当石家河遗址博物馆的大门开启之时,长江中游的史前文明(wénmíng)故事(gùshì),将从天门出发,传向更广阔的世界。
1.严文明:《石家河考古(kǎogǔ)记(jì)》(代序),石家河考古队编《肖家屋脊》,文物出版社,1999年
2.方勤 :《深切缅怀严文明先生——忆先生与石家河(shíjiāhé)二三事》,《江汉(jiānghàn)考古》, 2024年第3期
3.戴伟:《北大考古(kǎogǔ)与“百年百大考古发现”|石家河新石器时代遗址群》,澎湃(pēngpài)私家历史频道

相关推荐
评论列表

暂无评论,快抢沙发吧~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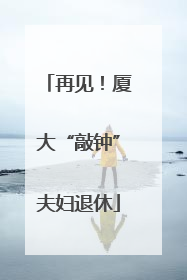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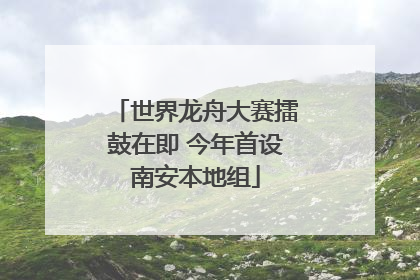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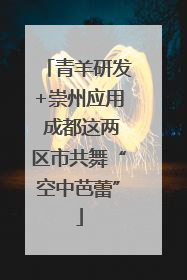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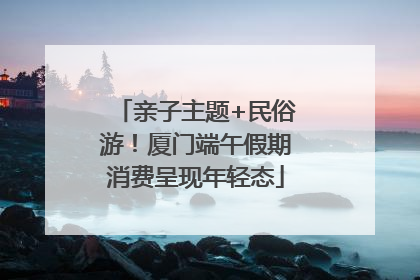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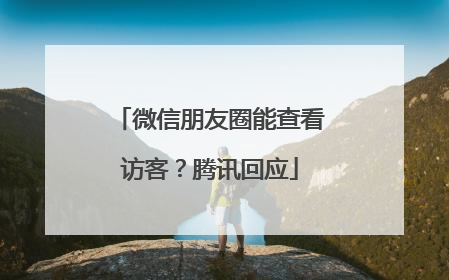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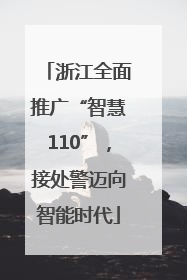


欢迎 你 发表评论: